我喜欢的新世界
他之前,哲学是乐观的,⼈也是。不管世界是什么,哲学都相信⼈能够完全认识它,甚⾄还能讲出来,让别⼈也认识。他之后, 哲学不那么乐观了,⼈也不了,因为世界的意思变了。他当然就是维特根斯坦了(Ludwig Wittgenstein,1889,4,26 -1951,4,29 ), 20 世纪最伟⼤的哲学家之⼀,或者就是最伟⼤的那位。此⼈ 22 岁在⽜津留学时就被认定为西⽅哲学最炫耀的新星,还⼀度靠遗产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富。
第⼀次世界⼤战始,这样的⼈当然不必上前线。但他却⾃愿海归,与炮灰同伴们在战壕⾥为伍,并多次⽴功受奖、⽕线提⼲。他也曾和希特勒同过学,读过相同的教科书,听过同样的⽼师讲课,但却学会了说不同的话。
认识世界是⼈⽣要务。在他之前,西⽅哲学认为世界由物质和精神两种事物组成,且都有个本质。认识世界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这个认知风靡世界、深⼊⼈⼼。即使是中国师长,如果不说点“看⼈看事要看本质”之类的话,许多都不会教书育⼈了。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哲学家则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在他们看来,认识世界是把世界上的事说得清清楚楚、听个明明⽩⽩。
下图显⽰的是维特根斯坦哲学⾥语⾔和世界的定义。其中,左边⼀列是世界,右边⼀列是语⾔;它俩完全“同构”。语⾔的核⼼功能是命题陈述。 命题显⽰的是⾔者认定的事实 。但事实的真伪,即命题的意义,就不是⾔者谆谆就为真了,藐藐听者也得认才成。不认,就徒费⼜⾆了。维特根斯坦认为,⼀个命题,只有当⾔者和听者可以通过逻辑对其真伪的认定达成⼀致,才能算说清楚、听明⽩了。这个命题才有意义,才讲出了它的意思,才 “可说”。如果⽆法达成⼀致,这个命题的真伪就模棱两可了, 也就没有确切意义,即 “不可说”了 。
在图⽰中,命题陈述的事实中的主客体,称对象。事态表⽰对象之间的深层逻辑形式,称为内涵。定义事态内涵的语⾔表达叫基本命题。事态内涵规定了基本命题的真伪,同时也决定了建⽴在其上的命题所陈述的事实的真伪或者意义。世上所有事,即事实的总和,构成世界。“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事物的总和”, 维特根斯坦如此断⾔。按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认识事物,⽐如说⼀艘船只能通过陈述它的具体⾏为以及它和其它事物的关系,即事实来完成,别⽆它途 。
与事实和⾮事实(幻觉、杜撰、想象等)对应的所有命题的总和则组成语⾔,说出⼈类对世界的全部认知。因此,“语⾔的极限就是世界的极限”。⾔者通过⼀系列命题,即⽤语⾔构建出⾃⼰对世界上所有事实和⾮事实的所思所想,然后再通过显⽰其逻辑形式的语⾔表达(即逻辑图像)告诉听者,因为逻辑是⾔者和听者通过语⾔交流的唯⼀共通基础。⾮逻辑形式的表达则既词不达意也不知所云,不能算语⾔表达。这么解释,实在太过于抽象。可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出过实例加于说明。
我举⼏个试试。⽂中所有例⼦都是我⾃⼰的杜撰。如果误读了维特根斯坦,错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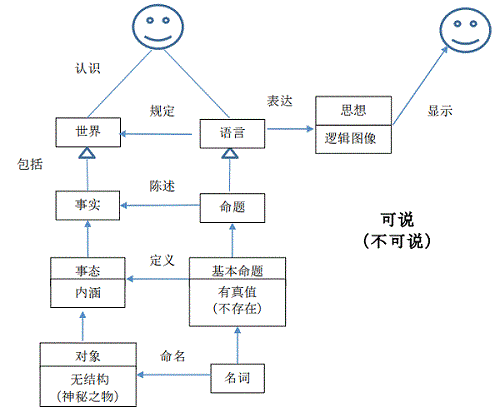
可说和不可说的世界
⾔者说事,⽤命题“有匹马长了⾓”来陈述有匹马长了⾓这个⾮事实;指⿅为马? 在语⾔哲学家看来,这个命题的事态内涵就是⽤“长了”把马和⾓这两个对象联系在⼀起的逻辑形式,说出来则是显⽰这个逻辑形式的⼀幅逻辑图像。当然,如果逻辑形式就不对,⽐如说,“有匹马下了⾓”这个命题就是逻辑不通的胡话了。但即使逻辑形式没问题,“有匹马下了⾓”这个命题的意义也并⾮由命题本⾝就可以决定。“因此命题中也不包含命题的意义,⽽只包含表达其意义的可能性”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那命题的意义该如何定呢?这就需要回到⾔者说事的⽬的上了。命题想表达的是⾔者对世界的认知。换⾔之,就是想通过命题让听者接受⾃⼰说出的隐藏在事实背后的事态内涵,即某种普世真理、普遍理念、⼤前提;或者说基本命题。维特根斯坦发明了⼀种从命题找出基本命题,并通过基本命题对建⽴在其上的命题的真伪进⾏判定的逻辑分析⽅法。其具体做法就是保持命题的逻辑形式,如果有需要,则对命题对象进⾏层层分解,最终使得命题所陈述的事实的事态内涵仅仅由“简单对象”确定。简单对象的意思是这个对象⽆结构不可分,即它是个孤⽴并有清晰边界的东东。道理不⾔⽽喻,如果⼀个对象不简单,是不可能把其的事态内涵,⽤逻辑形式表达清楚的,当然也就⽆法进⾏逻辑运算了。最终由简单对象描述的事态内涵给出基本命题。⼀旦确定了基本命题的真值,或真或伪,建⽴在其上的命题的真伪就可以通过递归逻辑运算得出。⽤维特根斯坦的话就是“⼀个命题总是其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当然,对命题进⾏如此这般的逻辑分析需要⼤努⼒。但只要努⼒够了,命题的真伪总是可以整清楚,意义总是可以弄明⽩的。
如果要对“有匹马长了⾓”这个命题进⾏逻辑分析,常⼈也许会接受马和⾓就是简单对象了,但哲学家不会。他们不承认马和⾓是简单对象,⽽会坚持它们仍然是有结构继续可分的,追问些“马是什么, ⾓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回答清楚, 他们不会罢休。逻辑分析⽅法要普遍适⽤,当然得经得起所有⼈包括哲学家的追问。
我觉得,既然命题说的是马的样⼦。把马和⾓视为⽣物体。分解到马和⾓的逻辑关系,或者说两者的事态内涵是由马和⾓特定的基因组合这个简单对象所决定的应该就⾜够了,今天的⼈,包括哲学家,⼤概都会接受了。也就是说,如果把基因当成简单对象,马和⾓特定的基因组合关系就确定了其事态内涵,决定了是匹马就 当成简单对象, 马和⾓特定的基因组合关系就确定了其事态内涵,决定了是匹马就得以不长⾓这样⼀个样⼦出现在世⼈眼前,从⽽⼀劳永逸地证实了“马长了⾓”这个基本命题的恒伪。有了这个基本命题,不管某⼈如何狡辩,其上的 “有匹马长了⾓”是个伪命题也就铁板钉钉了。⾄于规定马不长⾓的基因组合是什么,则是个科学问题⽽不是哲学问题。但只要相信科学,今天的⼈就都会认“有匹马长了⾓”是个伪命题。还不认, 那就⽆从谈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没有给不相信科学的⼈留位置,只是把决定命题意义的权威推给科学了。 换⾔之,指⿅为马的说法成不成⽴,不由研究本质的哲学家定,得由知悉事实真伪原因的科学家定。 有了科学,只要命题对象可以被恰如其分地分解成“简单对象”,⽐如说原⼦、分⼦、基本粒⼦、基因等,⼀旦科学研究出这些简单对象的事态内涵,规定它们⾏为的基本命题的真伪也就确定了。以此做基础,建⽴在其上的所有物理、化学、⽣物学以及⽇常⽣活⾥⾥的⾏为命题,即世界上的事是如何发⽣关联的,就都能说清楚、听明⽩,就都可说了。科学教科书不就是这么⼲的吗?讲事实摆道理不就是这么个过程吗?“但凡可说的,都能够说清楚。”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如此⼀来,维特根斯坦就把认识世界从认识事物的本质转化为找出对象的事态内涵了。认识本质需要“哲学王”的本事,⽽找出事态内涵则得靠科学家的努⼒ 。
本质试图回答世界是什么? 但上千年哲学王的努⼒从来也没产⽣出令⼈信服的答案。事态内涵只显⽰世界是什么样⼦的。⽤维特根斯坦的话就是:“我们只能谈到对象,⽽不能⽤语词说出它们来。命题只能说事物是怎样的,⽽不能说它们是什么。” 换⾔之,维特根斯坦没有传统哲学家那么乐观,认为我们可以知道世界是什么。他认为:语⾔最多可以通过陈述事实来描述世界是什么样⼦的,如此⽽已。
本质唯⼀但对象的事态内涵不,它随需要陈述的事实变,显⽰出世界不同的样⼦。 上⾯讲过,当谈到马的样⼦时,其事态内涵可以被视为某种特定的基因组合。但如果只是想认识马在奔跑时的样⼦, “马”这个对象则可以被视为⼀个⽜顿体。其事态内涵由⽜顿三定律这个基本命题描述。所有讲述马奔跑样⼦的命题如果符合⽜顿三定律就为真,否则就为伪。
为了完整,再补充⼀点。可说的还包括了维特根斯坦称为“重⾔式”的命题,其意义命题本⾝就可以确定,并不依赖于基本命题或者前提。这就是那些永远正确的命题,⽐如说 “今天可能刮风也可能不刮” 。不幸的是,不需要由基本命题来决定意义的命题也不包含对世界的任何认知,它们恒真。所以,说事时,如果⽆⼈可以证伪,千万不要沾沾⾃喜,以为⾃⼰说出了世界真理。很有可能只是说了重⾔式。它不帮助认知,唯⼀的意义就是⽆可辩驳。
可说的说完了。哪什么是不可说的呢?还是举个例⼦。丈夫对三位客⼈说 “我妻⼦长得美” 。对这个命题,⼀位客⼈可能附和,另⼀位不表态但⼼⾥就不同意了,⽽第三位可能还在琢磨这话的意思呢。说⽩了,就是丈夫并没有说出⼀个⼤家可以达成共识的意思,尽管命题明确显⽰了丈夫对妻⼦美的认知。但这个认知,别⼈就不⼀定能明⽩了。换⾔之,这个命题不可说。把命题分成别⼈可以听明⽩的(可说)和听不明⽩的(不可说),维特根斯坦为命题划边站队了。
命题“我妻⼦长得美”和“有匹马长了⾓”显⽰的逻辑图像同样清晰。“有匹马长了⾓”给划在“可说”⼀边,可为什么“我妻⼦长得美”就在“不可说”⼀边了?前⾯说过,可说的必要条件是命题对象可以被当成简单对象,或者说可以被分解为简单对象,从⽽可以得出定义其事态内涵的基本命题的真值。⽽“美”这个名词所指的对象并不满⾜这个必要条件。罗素把类似“美”这样的名词称为 “摹状词 the so and so”,因为它所指的不是⼀个简单对象,⽽是“如此这般”的对象集合。维特根斯坦则⼲脆称之为“神秘之物”。 细点说,妻⼦美的如此这般⼤致可以分解成⽓质、容貌、三围。⽓质和容貌依然神秘,三围好像容易搞定。但三围尺⼨如何才算美,由谁来定,定了是不是⼤家都会公认,就不好说了。这跟马的基因组合不同,科学可帮不上忙。要想找出⼀个普世标准来决定美的⽓质或者容貌,科学甚⾄都不敢尝试。⽽如此这般中只要有⼀个说不清道不⽩,普世的与美有关的基本命题就不会存在了。既然基本命题⽆真值,不确定, 建⽴在其上的“我妻⼦长得美”的真伪当然也就⽆法确定,于是就不可说了。
我之所以这么啰嗦是因为⼤家得知道维特根斯坦是位思维慎密的哲学家,⽽我也得讲讲我对他哲学的解读。简⽽⾔之,我认为他⽆⾮是说:认识世界靠⽤命题说事。除⾮是重⾔式,不⽤说。说时都得有个前提隐藏在命题后⾯,即基本命题 。命题说出的⽆⾮是建⽴在此上的逻辑形式,其意义或者真伪其实已经由基本命题定了。 然⽽,事要能说清楚、听明⽩却需要基本命题有确定的真值。这⽆法⾃证,哲学也给不了 。只有当事本⾝是 “可说”的,即研究事的科学能提供出基本命题的真值时,命题⽅能说清楚、听明⽩,才可说。否则,就不可说了。 因为基本命题真值的不确定,维特根斯坦把关于上帝、善恶、美丑以及哲学中的所有命题,⽆⼀例外地都给划到了“不可说”⼀边。 这,⽼⼦其实早 2000 年就说过:“道可道 ⾮常道;名可名 ⾮常名”。 维特根斯坦⽜的是:他是⽤数理逻辑追根溯源让我们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道”和“名” 。当然,他还多说了⼀句 “但凡不可说的,就该保持沉默”。 注意,保持沉默不是不说。⽐如说,当见到⼼仪的⼥⼦或者男⼦时,维特根斯坦可没有建议过保持沉默。“你很美”,这话必须得理直⽓壮地说出来,因为这话说出来并不是想让每个过路⼈听明⽩后参加⼀场决⽃,⽽只是表达⾔者的⼼意。维特根斯坦没这么傻,更不会这么蠢。想认识和表达那些不可说的精神事物的意义,乃是⼈的天性,更是哲学家的本能。
1919 年第⼀次世界⼤战结束,维特根斯坦也完成了⽤数理逻辑证明可说不可说的《逻辑哲学论》的写作。他想出版,但没有⼀个出版商愿意发⾏,除⾮他⾃⼰出钱。钱对他当然不是问题。但在他看来, “我的⼯作是写书,⽽世界必须以正当的⽅式接纳它”,于是断然拒绝。出版商让他找当时名声正旺的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给书写个序,书就能出版了。罗素欣然同意,并认认真真地读完书写了个长序。维特根斯坦⾮但没表达谢意,反⽽写信指责罗素误读了⾃⼰的书。宽宏⼤度的罗素仍然⼀⼿帮他免费出了书 。
书出版了,维特根斯坦认定哲学不可说了。劝⼈保持沉默,⾃⼰当然也不能例外。于是放弃哲学研究和遗产,进师范学校进修⼀年后就投⾝于奥地利偏远⼭区的初等教育了。这可并⾮⼼⾎来潮,乡村⼩学教师的⼯作他⼀⼲就是六年。他想亲⾝体验⼀下⾃⼰从 19-20 世纪浪漫⼩说⾥读出来的乡民的善良、质朴、智慧,更想改⾰当时以培养进城“打⼯仔”为⽬的的乡村教育。在他看来,孩⼦受教育的⽬的应该是提⾼她们的思辨能⼒ 。“他是⼀位天⽣的⽼师”,旁听过他的课后,他的姐姐总结到:“听他的课是⼀种享受。他不是单纯讲课,⽽是试图通过问答引导学⽣⾃⼰找出正确答案。”
维特根斯坦能⽤数理逻辑证明 “但凡可说的,都能够说清楚”,也很⾃信⾃⼰能给⼩学⽣讲清楚点可说的东西,教她们成为会思想的⼈。据说,少数学⽣还是能听懂他在说啥,但⼤多数学⽣就⼀脸懵圈了。 家长更是不明⽩这个穷得连个像样的屋⼦都租不起,也没有⼀个当地朋友相知,但却有带仆⼈开豪车的贵客周末登门拜访,上课不传授⼀点点有⽤知识的“怪⼈”究竟想⼲什么。在沮丧孤独中,当学⽣听不明⽩时,维特根斯坦打过男学⽣⽿光,揪过⼥学⽣头发。他不懂她们为什么就是不愿意主动思考,⽽愚蠢的家长们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的良苦⽤⼼呢?最终,⼀位学⽣被他打昏,早已忍⽆可忍的村民集体把他告上法庭。他只能放弃⽀教,不辞⽽别。多年后才回来向他当年体罚过的学⽣和她们的家长⼀⼀当⾯道歉。
不过,维特根斯坦的这段经历也给了我们这些凡夫俗⼦⼀点教训。如果连他这样的“天⽣⽼师” 都有讲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该知道当⾃⼰开⼜啰嗦那些可说或者不可说的陈词滥调时,别⼈有时候就会听不明⽩。责怪别⼈是蠢货,甚⾄还想打别⼈⼀顿的做法于事⽆补。更该懂得,善⼼善⾏的善果可以是所有⼈的痛苦。
六年痛苦的教书经历后,维特根斯坦当过园丁,还为姐姐设计监造了⼀幢精美的宅第,其间也参加了被称为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学术讨论。虽然写书时他就知道书中的话本不可说,以⼦之⽭攻⼦之盾不能算沉默。但和⼈讨论后,察觉到基本命题这个东东,没有逻辑之外的知识,有可能不存在时。他还是知道不太妙了,他的数理逻辑证明并⾮滴⽔不漏。⾃⼰从与剑桥⼤学教授们讨论哲学时⼀字不苟的可说,与战壕⾥⽂盲战友⽆话可说的不可说⾥琢磨出来的学问可能有点⽤⼒过猛,但却依然坚信⾃⼰认为哲学⾛上了歧路的看法没有错。
语⾔是⼈认识世界的唯⼀途径。当代科学⾰命让⼈们⽿闻⽬睹了科学探索认识世界的胜利,但推⽽⼴之就不会有胜利了。哲学研究不是科学探索,⼈间喋喋不休的真话假话、湿话⼲话更不是。崇拜科学,妄想在⾮科学领域⾥也同样依照科学探索的办法去说、去听,去认识世界⼤错特错。他这个天才的使命就是纠正这个错误。
尽管有⼈指出维特根斯坦早期和晚期的哲学思想截然不同,这个使命始终⼀脉相承。 为了完成这个使命,1929 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因为他还有话可说,哲学还有话可说。当时的普遍共识是,任何学问,⽆论是哲学、美学、还是宗教,其⽬的都是科学地构建出某种普遍性“理论”⽤来产⽣对所研究对象的⼀般性认识,找出普世真理,并做出有理有据的解释和推⼴。维特根斯坦后半⾝的哲学则是对这种共识的反动。他认为,除了⾃然科学领域,⼈类做学问的唯⼀⼯具,语⾔,不堪此⽤。 他决⼼从此不再建⽴任何理论,不再做解释,⽽是想通过显⽰语⾔在⾮科学领域⾥他称为“语⾔游戏”的⽤法,来阐述⾃⼰的哲学观点,⾄死不渝。追随维特根斯坦,下⾯我也⽤⼀场净化了的恋爱语⾔游戏⾥的三个阶段来显⽰⼀下我对他晚期哲学的理解。
第⼀阶段,考察三观。为此,⼀⽅表明⾃⼰相信上帝(天命、孝敬⽗母,…),但对⽅却吞吞吐吐说⾃⼰不相信。三观不合,不宜为友?三⾔两语之后,⼀清⼆楚。
⼀⽅相信的其实是那个当⼈需要时,⽐如说,维特根斯坦战壕⾥的⽇⽇夜夜,不请⾃来的⽆形上帝,⽽对⽅不相信的则不过是单亲母亲,三位⼀体的⼈格上帝,但却⾃信有与⽣俱来的良知⼀⽣相伴。这就不是个问题了。 换⾔之,相信上帝与不相信上帝的⼤是⼤⾮, 促膝谈⼼后就化成了乌有,⼀⽅相信的上帝和对⽅不相信的上帝摇⾝⼀变就成了共同,不可说可说了。谈恋爱如此,研究哲学或者⽇常交流难道不也经常如此吗?“ 词的意义是它在语⾔中的使⽤”,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如果不坚持⼀个词只有⾃⼰⼼⾥的⼀种意思,⽽愿意在⼀场语⾔游戏⾥仔细讲、认真听它的使⽤,⼤家有时候其实还是能说到⼀个意思上去的。
第⼆阶段,渐⼊佳境。其间,⼀⽅盯着对⽅的眼睛含情脉脉地说了三次“我知道你爱我”。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得看情况,对吧? 第⼀次说表达的可能是怀疑。“你真地爱我吗?”如果回答对了,你侬我侬,忒煞情多。第⼆次再说时对⽅只要点个头意思就到了。第三次说出时,对⽅就该有点表现 了。俗话就是:别只⽤脑,得⽤⼼观察,⽤⾝体去⾏动,恋爱才谈得下去。维特根斯坦对此的解读是:“不问意义,要问使⽤。不要去想,⽽是要去看”。 我觉得他说的是,命题传递的固然是逻辑图像, 但图像却可能清楚,也可能模糊,得依说话时的场境或者语境定,不能简单⽤逻辑分析来解读,也解读不了。
第三阶段,馈赠信物。⼀⽅拿出个苹果⼿机递给对⽅,对⽅推辞。“这是苹果不 是梨”,莞尔、笑纳 。但如果对⽅喃喃:“这跟梨有关系吗?”双⽅就不在同⼀个语⾔⽔平上谈了。当然,也可能是⽂化不⼀样。⽐如说,⼀⽅中国⼈,对⽅美国⼈,即使中国⼈改讲英⽂,“This is apple not pear”, 字⾯意思⼀清⼆楚,美国⼈能听明⽩则⽆可能。
这种由于认知障碍造成的普遍语⾔困境可以借⽤维特根斯坦的“甲壳⾍”来讲 。假如世界五⼤州有五种形象⾏为都不同但其实都是甲壳⾍的昆⾍。如果公之于众,⼤家公开透明地研究讨论它们⼀番,取个公共的名字,甲壳⾍,再公布所有研究讨论结果。以后⼤家再谈起这些甲壳⾍来,谁就都能明⽩谁在说啥了。这当然就是科学 。
但如果这五种昆⾍是被分别放在五个封闭箱⼦⾥的私货,只有箱⼦的主⼈能看见和知道⾃⼰的私货⾏为,其他⼈则⼀⽆所知。也没有甲壳⾍这个公共词汇和其它公共知识。在这种情况下,箱⼦的主⼈当然还是能讲出点⾃⼰私货的事。问题是,其他⼈能明⽩他是在讲⼀件关于所有⼈箱⼦⾥的“甲壳⾍”的事吗?恐怕不能吧?情况应该是,其他⼈顶多能⼀知半解点地听懂点与⾃⼰箱⼦⾥的那只甲壳⾍共通的事,对吧?
⼀个⼈的思想当然也是私货。当这些私念⽤带着⾔者独特的经历、⽂化、和智慧印记的语⾔说出来时,别⼈通常也只能⼀知半解,甚⾄完全听不明⽩。⽂化不同,有些话的意思是说不清楚的。经历不同,智慧不同轨,虽然使⽤同⼀种语⾔,但说的仍有可能是讲不通的⽂字。⽐如说,红楼梦⾥的林妹妹和焦⼤就说不通。林妹妹只能与和她说同⼀种⽂字的贾宝⽟交⼼。
实际上,如果谈恋爱只是为说清楚“我要和你困个觉”这个科学基本命题去摆事实、讲道理,罗列些意义⼀清⼆楚的辅助命题,不谈也罢,办法多得是。谈恋爱其实是⼀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着边际但乐在其中的语⾔游戏。谈的是⼼有灵犀⼀点通,你嗯我哼、你侬我侬,⽆关命题的真假对错。谈出的则是:在你之前,我谁也不想嫁(娶);在你之后,我谁也不会嫁(娶)的感觉; 亦不能⾔传,只可意会。
⼈类语⾔交流绝不是⾔者⽤逻辑上滴⽔不漏的命题告知听者些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么单⼀⽆趣,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错就在此。谈恋爱、讲哲学、话宗教是与说科学完全不同的语⾔游戏,⽬的和规则完全不⼀样。它们不告知真理,只求⾔者与听者的相互理解、互相认识、共同升华。语⾔游戏并⽆⼀成不变的统⼀规则,在哪场语⾔游戏⾥交流,就得按那场游戏的规则发⾔听语,切不可套⽤混⽤别场游戏的规则。每场游戏的规得由⾔者听者的⽂化背景、场景情景、以及交流的内容约定俗成。不幸的是,维特根斯坦的晚期哲学思想对我们太陌⽣。中⽂讨论⾥,套⽤混⽤规则发⽣太多。⽐如说,我就见识过⼀场关于⾃由意志的鸡同鸭讲的科学哲学对话,⼀⽅说科学,另⼀⽅讲哲学,谈的不亦乐乎,旁听的我⼀头雾⽔,因为我不知道是该按科学还是哲学讨论的语⾔游戏规则来解读双⽅的⼀招⼀式。
总⽽⾔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告诉我们。语⾔是⼈类认识世界的唯⼀途径。不能⾔表的认知是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所以,语⾔能说到的地⽅就是世界的边界了。不仅如此,你我还得知道,“我并不⾝处于我的世界之中,我的世界是我的疆界”。世界是所有⼈的, 我的所见所闻、所听所读、所思所想只能让我认识到我的那个有疆界的部分世界,即我的世界,你也如此。没⼈能知晓全部世界,但也没⼈会⼀⽆所知。有些事,除⾮⽣来此⼈此命,断⽆缘知道。有些事,没有亲⾝经历,绝不会明⽩。⼈类对于全部世界的认识只能通过每个⼈说出⾃⼰的世界来完成,别⽆它途。
说,如果仅限于⾔者⼀⾔堂的传道授业,当说的对象不是公共客体时,如果只允许说事实、讲道理,则⼏乎⽆话可说 。 科学以外,传道授业说的只是⾔者⾃⼰世界⾥的私念,绝⾮可以成为公认的事实。“这种语⾔的词汇命名的是只有说话⼈能够明⽩的东西;指的是他直接的、私有的感觉。因此另⼀个⼈⽆法理解这种语⾔” 不可说 。
不可说如果讲给思想领袖们听,就是警钟长鸣了,因为他们的梦寐以求就是把⾃⼰的思想全盘灌到别⼈的头脑⾥。但不可说的思想是⽆论如何也灌不进去的。维特根斯坦要他们闭嘴恰如其分。可如果“说”不再是⼀⾔堂的单向灌输,不再要求字字有意义,句句是真理,⽽是允许⾔者听者交流互动,真⾔假语,你说我听,我说你听、畅所欲⾔地参与⼀场场语⾔游戏,那么⾮科学领域⾥许多不可说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说的;恋爱可以谈出甜蜜,哲学仍然可以讲出智慧。
⼀⾔以蔽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彻底关上了思想独裁的⼩门,但却打开了⼈⼈平等共同认识世界的⼤门。真理是⼤家的,也是个⼈的。“我并不⾝处于我的世界之中”,任何⼀个⼈的世界都不是全部的世界,全部的世界别⼈也有⼀席之地 ,真理也许在别⼈的世界⾥。在⾮科学领域,⼀个⼈说出的任何想法,宣称的对,批评的错其实都绝⾮普世的对错,放之四海的真理。即使讲出个乌托邦来,那也只是⾃⼰世界⾥的乌托邦,别⼈并⾮就⼀定得喜欢。既然每个⼈的思想都是其独⼀⽆⼆的⽂化、经历和智慧的彰显,语⾔就该主要⽤来让说者听者相互欣赏彼此的⽂化,了解彼此的经历,学习彼此的智慧,⽽⾮追究彼此的对错,这不是选择⽽是必须。
别⼈世界⾥的对错你不会懂的。 “你只需要改善⾃⼰,这是你对改善世界唯⼀可做的”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个⼈能真正改善的其实只是⾃⼰的世界。别⼈的世界只能尊重,可以交流,但不可闯⼊,更不能占领。要知道,每个⼈的世界都是世界的⼀部份。要世界善,⼀个⼈⾃⼰就得⾏善。不要恶,就得⾃⼰摈弃恶。世界善恶的消长是每个⼈世界⾥善恶的总
和。每个⼈的世界善了,全世界也就善了。
1951 年 4 ⽉ 29 ⽇,维特根斯坦与世长辞。他最后的话是:“告诉他们,我有个精彩的⼈⽣”。这话可以当真,因为他给我们描绘出了如此这样⼀个新世界,⼀个我喜欢的新世界。

